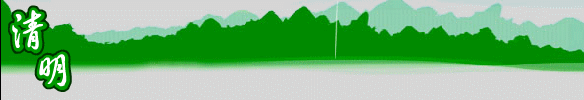车姓 囊萤堂车氏家乘全书
安实公支下为、之、应、发、世部分探微 |
| 探微汇总
韨佩流徽 安实公气宇轩昂样貌潇洒以外,在襄樊的生意做得也非常成功。正是安实公成功的生意为后面的几代人在安襄郧荆的风生水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安实公之后,家势发达起来,历经两次,在老家做起了辉煌宏大的宅第。屋宇俨然之中,大堂屋就有11间!牌匾很多,“韨佩流徽”是其中的一块,除此之外,还有“珍隆庋阁”“安宅永敦”“春永鹿门”等。“韨佩流徽”的意思大概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还要华贵显赫一点儿,虽然古代人都追求做官,鸿儒就是高官,高官都是鸿儒,但“韨佩流徽”强调的不是文化的优雅而是佩戴印绶的威仪。一个“流”字,既道尽了廊庙大器社会栋梁日理万机行色匆匆的风流神韵,又道尽了富贵人家丁口兴旺,人才辈出,父子叔侄在高屋大厦宵衣旰食进进出出的潇洒出尘。连大堂屋就有11间的府邸,想象一下吧,当然是名副其实的“珍隆庋阁”了。 繁衍生息在咸宁旧地、兴旺发达在安襄郧荆一带以及开基创业于天南海北各地的安实公的子孙永远不会忘记各位先贤! ﹡ ﹡ 古代长途交通一般依靠水路,“闯江湖”“打码头”等俗语就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那时,车家经黄石桥过金口入长江,再进汉江到襄樊,实属方便。襄樊自古为南北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商家必争之地。 春秋祭祀 百揆公身为河工(亦称堤工),直接上司是襄阳太守郑敦允,他们的关系特别好。这个太守的胞弟郑敦谨官至尚书,曾经做过湖北巡抚。他没有见到过百揆公,但在家里听哥哥讲到过百揆公,对哥哥和百揆公两人都非常敬重。郑敦谨在任湖北巡抚时来到襄樊,在襄樊指示在纪念他哥哥郑敦允的郑公祠里面给百揆公设置一个栗木牌位,命与郑公一起享受春秋祭祀,永享不替。 百揆公二十多年担任襄阳河工,负责岁修,实际上是襄阳治水的具体负责人,位高权重,更因德高望重。 百揆公自道光辛卯岁(1831)起开始任河工。1853年上半年应琼公接替百揆公继任河工。还有咸丰间应瑶公经理釐局,就是负责向来往船只收税。这样前后几十年,成就了一个河工世家。 襄阳重地,一个家族在那样的位置上几十年,不说别的,仅就连年岁修保证安澜的人员组织、技术指导和物资储备调配来说,就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 ﹡ ﹡ 这个《百揆老先生序并赞》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时候写的。百揆公还健在,故称“老先生”不称“公”。从这里还可以知道两件事情,一是在1836年的时候,百揆公让21岁的三子应琼和14岁的四子应琦由这个孟先生带着到苏杭一带旅游。二是在1837年的时候,百揆公本人回过一次老家,这个孟先生随行。 制台和府台 传说百揆公做的是湖北制台,还说他有一个干儿子,名叫顾家衡,做了府台。 制台是对总督的别称,实际上没有湖北制台,只有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清史稿》上面历任湖广总督、湖北巡抚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百揆公没有做到巡抚,没有做到总督。“年过七十,襄樊堤工难以再举”后获得过什么荣誉职位就不知道了。 顾家衡确有其人。南阳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就是他的杰作。他父亲顾槐是大书法家,被称为“前清第三支笔”。顾家衡在南阳武侯祠题联都署名顾嘉蘅。据说他世代定居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在车家乡下老人的口中还流传着一个关于顾家的顺口溜:“有人到了顾家畈,免粮三百担。”但车家现在没有人知道顾家畈在什么地方。 顾家衡在南阳武侯祠留下的题刻(包括上面提到的这副对联在内)至少有11处,其中6处署有时间,最早的三处署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最晚的一处署的是同治四年(1865)了,而百揆公生卒年是1878-1860,顾家衡做干儿子和做官,在年龄上是完全“合理”的。顾家衡被认为是家在襄阳而在南阳做郡守的,曾三任南阳知府,叫府台不为过。 自己做制台,干儿子做府台,这些传说怎么就神乎其神呢?不解之处只好任其散布成历史的迷雾了。 豪华丧礼 传说家道衰落起自一个太妈去世,大家从襄樊回籍大办丧事。 这个太妈是哪一个? 显然,二房的太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会是为二房的两个太妈中的任何一个太妈大办丧事。长房百揆公三个太妈,黄氏1833年7月11日去世了。继妣李氏是樊城人,于1808年8月12日去世,当时才22岁,更早。三妣赵氏也是樊城人,1805年2月16日出生,比百揆公小27岁,只生有应瑲公一个人,且宗谱上面没有记录殁葬,是因为给她大办丧事的可能性不大。 只有三房了! 三房继妣何氏只生有一个女儿,且宗谱上面也是殁葬未详的,可以排除。 这样就只有一个人了,就是三房太爹放斋公妣严氏。严氏1788年5月20日出生,享年77岁,1864年9月11日(旧历的八月十一日,准备过中秋了)去世。整个大家族中的七个太妈只有这一个太妈具备条件让大家来大办丧事: 放斋公本人在;三房的四个公子都是严氏生的,且二公子应瑶“保举六品衔,不论双单月郎选,从九品,例赠修职郎”,是应字辈的11个弟兄中地位最崇高的;这个时候,家大业大的贵族之家的超级府邸做好也有些年了;家族之中别的尊长已都不在了(长房百揆公1860年6月8日去世)。此时,放斋公一声号令,小字辈们宁不惟命是从! 母以子贵 安实公的长孙应瑚公是百揆公的长子,这个长房长孙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是百揆公继妣李氏生的,生下来一岁半的时候,母亲李氏就死了。这个李氏不是本地人,是百揆公在襄樊娶的襄樊的人,1808年8月死的时候才22岁。百揆公1860年6月去世,李氏与百揆公一起葬在猫儿山。推测这个过程,应该是李氏在襄樊去世,由于很年轻,又是暑热的8月,可能就葬在了当地。50年后,百揆公高龄谢世,儿子当家作主,家势又好,这时候生母还葬在他乡异地当然不行,必须迁葬,要魂归故里,要认祖归宗。李氏能与百揆公一起葬到猫儿山,还荣膺皇恩旌表,儿子应瑚公作为长子是决定性的因素。 而百揆公妣黄氏,本境人,也只能葬在牌头岭路边山了。估计的原因是她去世的日子在五月廿四日。“正三五七九,坟山不能动土”,但七日之后就到了六月,坟山就应该可以动土,难道没有条件放七日?农历的五月下旬了,天气太热了?外面的事情太忙了?外面的事情太忙了有可能。这个时候汛期到了,这是1833年了,1831年起,百揆公就负责起了每一年的防汛工作做河工了。 ﹡ ﹡ 猫儿山坟山地界: 顶上以山背脊为界,上横宽五丈八尺。下以土沿为界,下横宽四丈五尺。东以界碑为界,东直长十六丈八尺。西以界碑为界,西直长十六丈八尺。四处有碑为界。 慨承父志 百揆公于1831年开始负责襄阳水利的“岁修”。 应琼公的传里头有一句话,说:“壬子岁,贼逼淦川……后乱平,百揆公年过七十,襄樊堤工难以再举,(应琼)公慨承父志,乐倾囊以毕乃事。”壬子岁是1852年。查《清史稿》的《文宗本纪》,壬子岁,太平军七月二十四陷郴州,大举北上,长驱直入,八月中旬逼近长沙,十一月中旬陷岳阳,十一月廿七日陷汉阳,十二月十八日陷武昌。这壬子岁的十二月十八日是1853年1月26日了。那么,“后乱平……”就应该在1853年了。 1853年的年头,战乱暂时平息,新年的汛期还没有到来,这时候,百揆公本人退居二线了,应琼公三十八岁,继承父业走马上任做河工(堤工)了。 应琼公上任后把属于家里的资财拿了出去,拿出去了很多(“倾囊”),这个事情在应琦公的传里也能找到佐证:“盖自令先尊君百揆公,抱奇才,甘心市隐,持筹握算,小试谋猷,以累巨万……其后,以湘(襄)水泛溢,筑堤防卫,财力俱竭而声施因是灿如。”应瑶公还有“创设启善堂,遍施粥食,活全无算”的善举。 这一家子都争着把东西往外面拿,这是为什么?都只是简单的换荣誉?照“财力俱竭而声施因是灿如”的“声施因是灿如”说来,也的确是换得了美名了,但事情一定不只是换荣誉这么简单吧。 辉煌举业 第一代安实公本人“幼习耕耘……壮奋四方志,寄贸樊城”,只是一个生意人,没有功名。 第二代兄弟3人: 之熙(百揆),贡生。 (继妣李氏皇恩旌表。) 之烈(名伟),从九品。 之勲(放斋),太学生。 第三代兄弟11人中9人取得功名: 应瑚(锦堂),太学生。 应璜(继周),太学生。 应琼(成储),邑庠生。 应琦(宝山),太学生。 应瑲(燦堂),太学生。 应璧(炳堂),从九品。 应瑶(西池),保举六品衔,不论单双月郎选,从九品,例赠修职郎。 (妣胡氏例赠孺人。) 应瑺(华玉),太学生。 应琇(辅廷),太学生。 第四代兄弟25人中5人取得功名: 发衔(子衡),军功保举五品。 发枝(桂林),从九品。 发铨(衡卿),子阳府廪生即用训导。 发荣(春田),军功保举六品。 发镇(抚臣),太学生。 第五代兄弟31人中1人取得功名: 世恩(荣轩),军功保举六品。 第四代和第五代6人的功名,其中3人由军功保举。 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像《红楼梦》里头的一个说法,叫“烈火烹油”。 婚姻家庭 1、就所谓原配而言,男小女大是普遍现象,这大概就是“女大三,抱金砖”意识的结果吧。据说女的年纪大一些,在生活上会比较照顾男的,男的会比较幸福。其实,这是现代社会的解释。在古代社会这样子的年龄结构是为再娶留下的伏笔。发铃公(1851.1.30)小于妣王氏(1846.2.22)整整5岁,小于女方4岁的就很多了。 2、女子的平均年龄很低,有明确纪录的这些人花样年华纷纷凋谢: 之熙公继妣李氏22岁。 应瑚公妣杨氏34岁,继妣熊氏46岁。 应琼公妣王氏42岁,继妣程氏48岁。 应璋公妣杨氏22岁,继妣蒋氏27岁,三妣张氏25岁。 发銮公妣王氏37岁。 世汇公妣陈氏22岁。 发铃公妣王氏28岁,继妣龙氏28岁。 发仁公妣刘氏39岁。 发枝公妣余氏29岁。 发铨公妣廖氏27岁。 发荣公妣严氏36岁。 3、少数几个太妈在太爹英年早逝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倒活了个寿享遐龄的。 二房明伟公曾在三兄弟之外以一个人的力量一次性买下七都余家港位于南溪畈的庄田105块,庄屋1栋(两重邻三)以及水塘三口,这个买卖的约纸的原件父亲看见过。后来卖给了上门南溪畈。南溪畈内部为水塘闹矛盾时亲戚来拿去了这约纸。 父子早殇 二房名伟公在1831年5月29日英年早逝,享年49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欣欣向荣的家族猝不及防,也让二房的子孙面临现实的困境,必须艰难地行走在长房和三房的树林之中了。 应璋公是二房的长子,在安实公总共11个孙子中排行第三,原本朝前可谓大树下面好乘凉,朝后可以傲视同侪,处在养尊处优的位置的。可是,17岁的时候,自己的大树倒下了。 应璋公小于妣杨氏整整四岁,这是再美不过的安排啊!可杨氏1832年才22岁就去世了,这时应璋公18岁。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应该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没有留下子嗣。还是一个18岁的男孩儿,一定还没有成熟到懂事,所以,只记下了杨氏生卒的年份,没有记录下其生卒的月份、日子和时辰。 继妣蒋氏1816年3月20日出生的,1832年17岁。三妣张氏1818年出生,1832年15岁。她们什么时候来到应璋公家不知道了,但她们都在10年后的1842年去世,一个终年27岁,一个终年25岁。 蒋氏是在10月19日生下儿子发仁70天后于12月29日去世的。张氏是7月份去世的,是樊城人,就地葬在樊城。 可以推测,可能蒋氏一直住在老家,身体不好,又没有生孩子,这个时期应璋公本人在樊城,是在樊城娶的张氏。 玉孤之成 1842年的下半年,28岁的应璋公一定很凄惨。距离妣杨氏去世整整10年,继妣蒋氏在老家、三妣张氏在襄樊先后亡故,现在,上面是两个将近60岁的寡母,下面是一个不足百日的孤儿。 不知什么时候余氏来到了应璋公家。余氏1822年7月2日出生。余氏1845年3月31日生下发义礼门公,1847年7月4日生下发礼公。 1850年5月19日,36岁的应璋公留下分别为8岁(发仁)、5岁(发义)、3岁(发礼)的三个儿子,还有67岁的母亲徐氏和66岁的二妈施氏,撒手人寰。这一年,余氏29岁。 1854年7月27日,徐氏去世,享年71岁; 1860年11月18日,施氏去世,享年76岁。应璋公四妣余氏1880年3月9日去世,享年59岁。 ﹡ ﹡ 小时候,看到家里有纺线车一台台的摆在堂屋里是有些感到奇异的,由于没有在别的人家里看到过,当时还有几分自豪感。几个缠足的老奶奶先把摘回来的棉花请弹棉絮的师傅弹过,然后做成油条一样的捻子,然后就用防线车纺成线。成品是一个个绕在棍子上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白白的大萝卜一样的“线锭”。“因思世之身为男儿,家称颇有,忍令其子事田舍,昧之无以视,孺人之贫而玉孤之成,相去为何如哉!”真是让人振奋。“累年束修之与膏火,悉取给于孺人之纺织。”原来也有这么多的辛酸。 岘山一碑 有关西池公的一些情况较为有影响。 第一,西池公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直接指示下做牙釐局的负责人,负责向来往船只征税的工作,又“创设启善堂”。而本人外科医生又做得好,医术高,为“总制”(湖广总督)和“观察”(道台)看病,手到病除。都颇获好评,颇得信任。 第二,长子发铨1831年8月13日出生,自己却娶了一个1832年2月29日才出生的继妣胡氏,结果,小儿子发锐比几个孙子都小。但是,不幸的是在自己58岁的时候,老年丧子,长子发铨44岁在前途无量时故去。西池公救过多少人的命,却救不了儿子一命! 第三,前后两任安襄郧荆兵备道给西池公写传赞,前任安襄郧荆兵备道张之渊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胞兄,现在是来任命新的安襄郧荆兵备道,经过襄樊,自称愚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问题是,谁是联络人呢?自己64岁时去世了,长子去世更早,小儿子发锐1870年出生,也就十二三岁。那么,是这时大约50岁的继妣胡氏? 第四,西池公行医,应琦公行医,在家族就形成了中医药的传统。彭妈,缠过脚的,经年累月扶一把椅子在野外采摘金银花、半夏、车前子等药材;三伯父裕盛公是县中药材公司的采购员;族兄传金无师自通在县中医院做医生。老屋有一个越爹开过“春和堂”。 神秘三房 安实公三个儿子分为三个房头:大房百揆公、二房名伟公、三房放斋公。 大房正可谓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百揆公事业成功,入祀立传,极尽尊荣。高龄谢世,至今保持安实公子孙中享年最高82岁的记录。族谱中作《百揆公传》的余澄清是长房长孙金坡爹的学友,此人当时为候选儒学,正做县志的编写工作。真是人才济济,一呼百应啊! 二房一开始时以名伟公的从九品的功名是可以聚焦众人的目光的,但马上就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多灾多难。名伟公本人49岁英年早逝,应字辈的兄弟二人也分别于36岁、43岁早殇。几代孤儿寡母,到发义礼门公还能学有所成,望隆当世,实属不易。 三房比较神秘。放斋公在族谱上只有一个《赞》,是姻(结拜)兄弟写的,看语气,时间在第一次创修族谱放斋公本人还活着的时候。据说刘端山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房的孝子孝孙的名字,世字辈的有二十多个人,可族谱上面三房世字辈的只有11个人的名字。还传说三房的子孙最后一次清明节从外地回老家祭祖,是直接到刘端山上祖坟,并不回祠堂拜祭,也不回祖居会见亲族,从此了无音讯。 安实公之后,家族慢慢地由三房演变成了在老家和在外地分别发展的两股,这两股人马的守业创业的兴衰利钝是各自的还是互相的?故事应该很多很多…… 风流余韵 金坡爹发銮公“殁葬失考”只能说是历史的无奈。刘端山的坟茔清清楚楚的,怎么写着“失考”呢?原来现在的族谱是转录的光绪癸未年(1883)续修的族谱。由于1948届族谱的灭失,那么多的人,除了极少数的能在坟山指认出坟茔以外,也实在是“殁葬失考”了。 发銮(金坡)公、发铎(振文)公、发义(礼门)公、发铨(衡卿)公可谓最后的贵族了。 发铨公是发字辈年纪最大的,借助家族在外面的基础发展,任“子阳府廪生即用训导”,势头不亚于前辈,可惜44岁亡故,这样,从安实公创业襄樊以来,在安襄郧荆的百年基业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发铎公、发义公在老家不甘穷乏,发奋图强,读书立业,成为乡贤。发銮公(生母胡氏樊城人)在襄樊长大,终又回到老家。到世字辈,只有一个世恩公,由军功保举六品衔,总算还有一点儿流风余韵了。 发銮公发义公他们为家族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将安实公升葬到了牌头岭。 ﹡ ﹡ 余友金坡兄,风雅士也。工书、善画,于丝竹之事靡勿精,茗碗炉香罔不备。且性最静,好读书,不求甚解。从先严游。曾与予共砚席,每当诸友聚谈,谐谑杂出,而兄但闭户默默不知其在室中作何营纪,倾听良久,惟时闻繙纸飒飒有声。既而,肄业襄樊道里,悠悠七载,于兹行复相见……(余澄清) 做房子的时间 第一次做房子,一定是在1831年名伟公去世之前或当时,只有这样,才好解释传说当中的两次做房子相距时间很长、更换大门楼、安实公升葬等一连串充满传奇色彩的事情。 第二次做房子是在什么时候呢?第二次做的六重这边有一块砖上有“道光庚戌”的字样,是制砖的年份。附近没有大型的窑址,所用青砖的型号又很多,又用了不少的泥土砖,还有五重这边铺地的大方砖在六重那边完全没有用到,种种迹象表明那些砖是从外地运回来的。这样,做房子就一定在“道光庚戌”(1850)之后了。 传说世武公的太妈帮了工,世武公住的那房子就是百揆公他们作为答谢在房子做完后把多余的零碎的材料给这个太妈做的。这是又一个重要线索。 世武公的太爹之廷公妣袁氏已于1824年2月6日去世,到之廷公去世的时候只有继妣孟氏在。孟氏1807年3月9日出生,1853年之廷公去世时47岁。之廷公与百揆公兄弟是堂兄弟的关系,孟氏这时中年得力,又有三个儿子,估计帮工应该是真心的帮了忙。那么,做房子应该是在1853年之廷公去世后了,否则不会说成是给那个太妈做房子而应该说成是给那个太爹做房子。 1853年的年头,应琼公继承父业走马上任,百揆公本人退居二线了。百揆公退休后,回原籍做房子以养老,比较合乎情理。 居住分布 第一次做起的房子只有四重,分布就简单了,一重做祖堂,兼接待宾客,也许还有安实公的继妣余氏居住。余下的三重兄弟三人三个房头,一个房头一重。 第二次做房子是在第一次做起的四重的前面加一重,把四重变成了五重,再紧贴着五重的西墙做起另外的六重,一共就有了11重。 三个房头的分布: 首先说二房,1853年之后房子做起来的时候,名伟公早已经不在了,二房的长子应璋公去世的1850年正是做准备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也死得不是时候,剩下只是寡母两人,稚子三个。还有一个应琏。所以,当然只能住1重了。原先只做四重的时候,住了一重,现在没有力量在扩大规模做房子的事情上做贡献,也只能住一重了。这就是五重这边的最后面的一重。 长房,百揆公在,五个儿子在,他是一家之主,退休在家,要接待客人,要供奉祖宗牌位,没有7重摆不开,这就是六重这边的全部和五重这边的前重。 还剩下五重这边的中间3重,就归了三房。估计放斋公一重,自住兼接待,四个儿子两重,两个儿子合用一重。年龄上都差不多,为什么长房的儿子一人一重而三房的儿子两人才一重呢?可能与出资以及今后是回老家还是继续在外面发展的长远规划有关。传说三房出去的人比较多,也正好印证了这样的推测。 珍隆庋阁 做房子显示了富贵之家强大的势力,仰仗了官府的力量。 村里人不眼红就不会不给予一定的方便,可就是为了司空见惯的一小块地基之争,具体说就为了半间房屋的地基,闹到人家说你家有钱,就是堆那么多的黄金,我们也不辏圆。那个通过用大缸种南瓜打赢官司的传说如果属实的话,就是典型的一手遮天,因为那明摆着属于掩耳盗铃。 外墙皮一米多高的红石条是江汉典型的堤防用料,武汉司门口码头一带,现在还能看得见用那种红石条砌的长江堤岸。做房子的全部材料,所有的砖瓦、石材、木料,都应该是外地运回来的。那个建筑物的设计施工监理等等,应该全部是正规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可能是乡下工匠。世武公的太妈帮助看看场子以及给工程队烧火做饭,很可能是唯一在那个工程中做了事情的车家人。用了那么多的土砖,估计是计划没有作充分,有些情况没有想到,青砖运回来少了(比如前重的地基那么深,都是用的砌墙的青砖垒起来的)。要说是金木水火土的讲究需要用上一些土砖的话,只要点缀一下就行了,像谷仓等地方为了防潮是必须用到土砖的。 这些都是百揆公退休后应字辈的人做的了。而第一次做起来的四重更豪华,更精致,动了雕工,堂屋铺了金砖,则“从九品”的名伟公有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急流勇退 传说车家的得力人从襄樊回到老家给一个太妈大办丧事,等到一两个月后再回到襄樊,别人把几条街的生意改换门庭据为己有了。打官司又糊里糊涂输了。于是,家道急转直下。 前面论述过是放斋公带一家子给严妈办丧事。严妈殁于同治甲子年八月十一日(1864.9.11)。 应瑶公从咸丰到同治是步步高升。由于他医术高明,省城的“总制”(湖广总督)患病后专使聘请,他没有去,“总制”就以巡视边陲的名义亲自来到襄樊就诊。还有“观察”(道台)“闻名晋谒”(看病)。两人还都送了厚礼。“观察”还亲笔题联相赠:“著手成春,暗与道合;怀才济世,清畏人知。” 宗谱上面有张之渊给应瑶公写的传,张之渊在传里表达了对应瑶公十分的崇敬。这样的架势,到1883年续修族谱的时候(可能提前一两年)还能请到张之渊,应该不会是输了官司的。 郑敦谨做湖北巡抚是同治四年(1865)四月初五日己巳(4.29)到十一月十一日壬申(12.28),中间有一个闰五月,总共是243天。郑敦谨在襄樊指示把百揆公的牌位放到郑公祠里面去的时间是在1865年年中到下半年这一段时间。 财产纠纷官司不是简单官司,很快就判,即刻就接受明显不分是非的判决,不合情理。 应该不存在输官司的问题,一定另有隐情。 入土为安 安实公殁于嘉庆丙子年十二月初八日(1817.1.24)辰时,葬牌头岭路右边山。其实,安实公首先就葬在刘端山,再升葬到下边园,最后才升葬到牌头岭。 刘端山是祖坟山,又葬到了风水,升葬到下边园,传说是因为刘端山的人迁到高桥的刘子才后,出了一个太监,可能会来掘坟。估计应该还与名伟公1831年5月29日英年早逝等有关。 还升葬一次,升葬到牌头岭,传说是因为下边园是军地,军地葬坟,子孙去当兵,不好。据族谱记载,安实公子孙短时间内当兵而由军功保举五品六品的有三个人,当兵没有当出名堂没有记载的一定还有多人。 成储公妣王氏葬刘端山安实公废穴。王氏是老屋王燮谋人,42岁,殁于咸丰戊午年正月十九日(1858.3.4)辰时。这很不好理解,阴阳先生害的? 母子合茔。罗母指的是成储公三妣罗氏,樊城下首龙坑罗宅人。生未详,殁于同治壬申年九月廿一日(1872.10.22)卯时。发鍈是成储公三子,王氏所生,殁于同治壬申年九月十九日(1872.10.20)酉时。九月坟山不能动土,只好葬屋下首;一家母子一前一后去世,中间只隔两天,虽然不知道这个罗母多大岁数,但儿子是17岁,正一出之阳的年龄,这是很惨的。但也无合茔的道理,不可解。 成储应琼公葬所无记载也属不可解。 故事里的事 那年刚巧发大水,水到门口塘的塘塍。建筑物料是放排来的,底下是木材,木材上面是石材。 五重这边的中堂上面挂一块“安宅永敦”的大匾,抬头是“放斋老先生德配严孺人新居落成”。六重的中堂上挂了两块匾,分别是“韨佩流徽”和“珍隆庋阁”。人们不认识这个“庋”字,向严壁成先生请教,严先生说:“‘庋’字!”人们以为严先生说的是“‘鬼’字”(庋、鬼同音)。抬头称百揆公为“伯父尊庚伯”的顾嘉蘅送的“匾对”(条屏)一共是10条,上下联2条,中间文章8条,老屋的裕金公结婚的时候还借过来挂过,落款顾嘉蘅三个字清清楚楚。 富的时候生活过得好,八月中秋一过就开始采买置办年货。家里的“捡坛”(一种方便收藏食品的肚大口小的坛子)很多。冬天沟坑里一层白的是泼洗锅水后凝结的猪油。穷了后,五重这边的后重堂屋挂的“春永鹿门”的匾被“洗金”,整个房顶的瓦被“赶罾”卖钱。 对应六重,在外面分别另做了厨房。但现今看不到什么废址等迹象。 建筑中体现祈福求财宗法等级意识的情节: 改换大门楼,弃用鼓礅。 下水道一重走左一重走右。一重之内也不走直线,在堂屋地下绕弯。 前人留下遗言,子孙穷了可以拆了房子卖钱,但不可以整个房子卖给外人让外人住进来以致失去地基。 家与国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地位很高,可是湖南曾家的房子与车家的房子比较起来差远了,根本不在一个境界上。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朝廷重臣的身份率军打仗正处在高峰期的时候,他一大家族的人在老家做房子。就做房子这件事情,曾国藩在家书中给家里人提出种种具体建议,甚至连门口的对联都给作好,极尽操心。但是那个房子实在很简陋,没有超出遮风避雨的层次。 车家,房子规模宏大,雕梁画栋,从建筑理念、布局安排到“庑架”(排扇)、天井、沟坑结构再到物料运用等等都独具匠心,堪称建筑艺术的精品。车家人几十年具体负责做工程,设计规划、工艺标准、建造监理等等都驾轻就熟一呼百应。当然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规模宏大就必须用上超大的木材构件,雕梁画栋也是木料构件,大量木料的运用使得房屋的寿命大打折扣了,因为木料易腐朽,又招虫害,维护成本高。这就是曾家的房子还在而车家的房子濒于消亡的原因了。真是人意斗不过天意。 族谱上面,之、应两代太爹太妈中很多人都有“传”“赞”,可是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提到做房子的地方,好像房子早就在那里似的,似乎所有人都很超脱的样子,这是为什么?是做房子的费心费力的主持人根本上就不是车家人,比如是派来的工程项目经理?是回避,不愿意提? 清朝官制 清朝省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称巡抚,又叫封疆大吏。巡抚之上设总督,总督一般辖三省或两省。总督侧重于军事,称“制军”,也叫“制台”,又有“帅”的称号。巡抚称“抚台”,不能称“帅”。总督所驻之处是总督衙门,又称“督院”,巡抚所驻之地称抚院或抚衙。 巡抚和总督开始只是临时的差使,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全称为“布政使司布政使”,像古时候的一方之伯,又称“方伯”;也像天子的屏藩,又称“藩台”。巡抚和总督固定后,布政使的地位就降低了,成为巡抚和总督的僚属了。 一省之中还有专管司法的“提法使”或称“按察使”,全称为“按察使司按察使”。“按察”相当于古之“陈臬”,因此“按察使”又叫“臬台”。“臬台”的地位仅在“藩台”之下,“藩台”和“臬台”合称“二司”。抚台、藩台和臬台称“三大宪”,巡抚就有一个别称叫“抚宪”。 总督和巡抚的僚属还有专管教育的“提学使”,又叫学政;专管盐政的“盐运使”等,地位比“藩台”和“臬台”低。 司之下设“道”,如粮道、盐茶道、兵备道、川东道等。道又称“道台”,因为相当于宋时的“观察使”,所以也称“观察”。 清朝的官员分九品,总督为一品,巡抚二品或从一品,司三品或从二品,道四品,道的地位恰是处在承上启下的一级上。 族谱创续及其他 经仔细阅读族谱序言,审阅传世族谱品相,参考传说,慎重稽核,确信族谱《车氏家乘全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创修,光绪九年(1883)秋续修, 1948年第三次续修, 1993年下半年的续修是最近一次续修。 光绪九年(1883)续修族谱的时候,安实公支下的发字辈和世字辈56个子孙除了夭折的早殇的英年早逝的或当兵到外面不知所终的以外,一般都正健在,自然不会有殁葬的纪录,这个纪录应该是1948年这届族谱的事情。可是1948年续修的族谱遭到了文革的劫难,只有一本幸存了下来,是宽字辈部分的。到1993年续修族谱的时候,除了这本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关于宽字辈的记录可资利用以外,基本上是跳过1948年那一届族谱而直接抄录了光绪九年(1883)的那届族谱。于是,原本在光绪九年(1883)没有纪录而到1948年应该已有了记录的地方,又回到了光绪九年(1883)没有纪录的老样子了,从此变成“未详”“失考”了,也就是说,凡是1883年续谱之前没死的续谱之时健在的都“未详”“失考”了。 呜呼! 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只是一介草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与国家没有关系。家族轰轰烈烈的生意没有继续做下去,那么多人去当了各种各样的兵,等等,都是因为国家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啊! |
族谱资料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929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930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932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936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937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1027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1029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1491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1492号) | ||
| 【1426号谱】族谱资料(总1493号) | ||